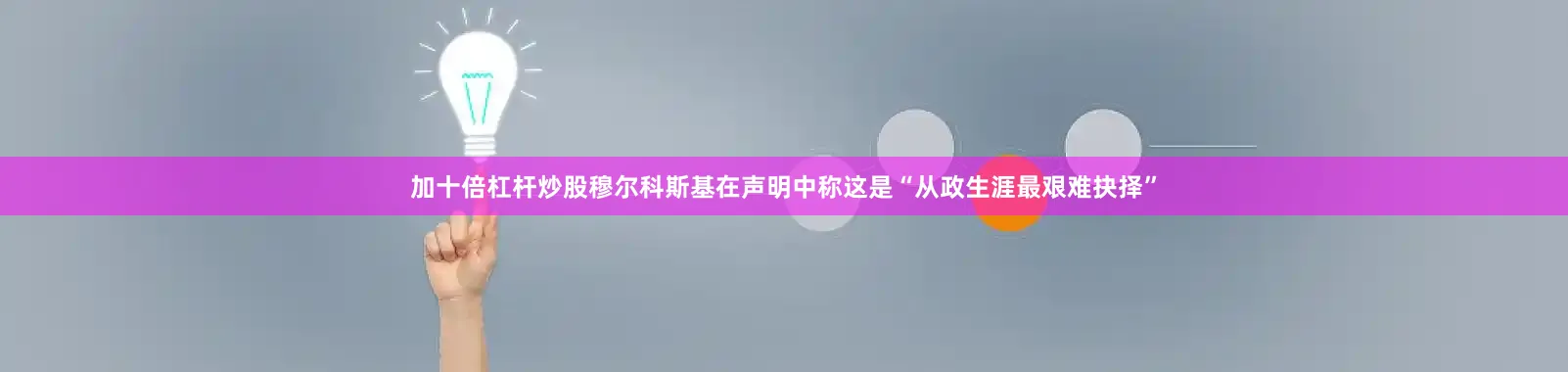《鲜于璜碑》作为东汉隶书的经典遗存,其墨色表达并非直接的笔墨书写痕迹,而是通过碑刻拓本这一特殊载体,将刻石的肌理与书法的精神凝结为可视的墨色意象。探讨其墨色表达,需跨越“书写-刻石-拓印”的三重转化,从物质载体、笔法映射与审美精神三个层面,解码汉隶墨色的独特内涵。
图片
一、拓本载体:石质肌理与墨色层次
《鲜于璜碑》的墨色首先源于碑石与拓印技术的互动。碑石自东汉建光元年(121年)刻成后,历经近两千年风化,石面形成了自然的剥蚀与凹凸:笔画凹槽深处因不易磨损,拓印时墨色饱满沉厚,如“点”画的圆劲收笔与“横”画的中段,墨色凝聚如漆,显露出刻石时“深刀刻入”的力度;而笔画边缘及石面漫漶处,因石质疏松或磨损,拓印时墨色渐淡,甚至出现“飞白”般的虚灵感,如“撇”“捺”的末端,墨色由浓至淡的过渡自然如呼吸,恰似毛笔挥运中“力尽而势未尽”的余韵。这种墨色的浓淡对比,本质是石质肌理的“拓印转译”。碑文中“璜”、“君”等字的笔画交接处,因刻石时刀锋的叠加形成细微的刻痕起伏,拓本上便呈现出墨色的“重影”效果——浓墨中隐现浅淡的层次,既非刻意的笔墨调控,也非拓工的技术误差,而是石质、刻工与时间共同作用的“自然墨法”,让静态的碑刻有了“屋漏痕”般的生命质感。
二、笔法映射:隶书体势与墨色节奏
尽管《鲜于璜碑》的墨色依托拓本呈现,但其内核仍是对隶书笔法的忠实映射。东汉隶书“蚕头燕尾、一波三折”的典型体势,在刻石与拓印中转化为墨色的节奏变化:起笔处“蚕头”的藏锋逆入,刻石时多作圆厚的弧形凹槽,拓本上墨色沉凝如握拳,呼应书写时“笔锋蓄势”的凝重;行笔至“波磔”处,刻石刀锋渐展,凹槽由深转浅,拓本墨色随之由浓趋淡,至“燕尾”收笔处,刀锋重按深刻,墨色再度聚敛,形成“重若崩云—轻如蝉翼—凝若坠石”的三段式节奏。 这种墨色节奏与笔法的呼应,在“鲜于”二字中尤为显著。“鲜”字右部“鱼”的横画,起笔墨色厚重如“蚕首”,中段行笔墨色稍浅显舒展,收笔“燕尾”处墨色骤浓,恰似毛笔在绢帛上“提按顿挫”的动态留存;“于”字的竖钩,起笔墨色圆浑,中段墨色匀净如“锥画沙”,钩处墨色因刻石转折的锐角而稍虚,暗合“转笔换锋”的书写逻辑。墨色在此成为笔法的“视觉回声”,让早已消逝的书写动作在拓本上重生。
三、审美精神:汉代“雄浑”气象
《鲜于璜碑》的墨色表达,最终指向东汉的时代审美精神。汉代文化以“大美”为尚,崇古朴、重气势,这种精神在墨色中体现为“厚而不滞、雄而不野”的整体气象。与后世帖学书法追求“笔墨韵味”不同,其墨色不刻意求巧,而以“质”取胜:通篇墨色以沉雄为基调,浓墨处如古鼎彝器的包浆,透着岁月的厚重;淡墨处似远山含黛,不飘不浮,与浓墨形成“刚柔相济”的张力。 这种墨色的雄浑感,与汉代画像石的粗犷线条、青铜器的饕餮纹饰一脉相承。碑文中“君”、“讳”等字的笔画,墨色饱满如梁柱,却因石质的自然剥蚀生出细微的“飞白”,使厚重中见灵动,恰似汉代宫殿的梁柱——既具支撑天地的雄浑,又因木纹与风化显露出生命的肌理。墨色在此已超越视觉元素,成为汉代“天人合一”审美理想的物质载体:它既是人工刻凿的痕迹,也是自然风化的结果;既是书法精神的凝结,也是时代品格的投射。总结《鲜于璜碑》的墨色表达,是“书写意—刻石形—拓印色”三重转化的结晶。它以拓本为媒介,让石质肌理成为墨色的“天然笔意”,让隶书笔法成为墨色的“内在节奏”,让时代精神成为墨色的“灵魂底色”。这种跨越千年的墨色意象,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汉隶“力与美”的视觉范式,更揭示了中国书法“墨见笔、笔见心、心见道”的深层逻辑——墨色从来不是孤立的色彩,而是文化精神的可视印记。
图片
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。
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
这首古诗主要以《鲜于璜碑》的风格进行创作,偶尔参合一些《张迁碑》的风格,侧重于墨色的变化与对比,局部小章法形成块面感。落款为“岁在乙巳秋,游庐日课”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“毕竟与四”四个字形成一个小章法,饱蘸墨汁写“毕”,与“竟”还有“与”的枯笔形成鲜明对比。作为全篇第一个字,结构上基本平稳,内部做一些微小的律动。“竟”整体取纵势,与平稳方正的“毕”形成对比。多横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方向,字内空间形成律动。“与”整体取纵势,与“竟”呼应,“与”上部的五个点随机分布,多点不同方向,更显自然和趣味性。“四”笔画减少,故写的粗厚重一些,与“毕”形成呼应。“与四碧映”的“碧”饱蘸墨汁,写的茂密一些,与“四”呼应,“碧”是上下结构带有左右结构,整体较为整齐一些,上部的“王”做左放右收的放射状,“白”的一点要搭接的轻盈一些,下部的“石”的撇还是采用搭接的方式更显方厚,“石”的“口”写的方且厚重,更显古拙朴茂。“时同日荷”的“时”左右结构,浓墨重笔,左小右大,三个横画取不同方向,上面的为往上翘,中间的平,下面的往下走。“同”的最上面的那一横取中间凹两边翘的写法,采用搭接的方式写出来,撇左弯,右竖直,曲直结合,动静结合。“荷”采用篆书写法,使得整个字更加的茂密,草字头写的左大右小,整体宽扁,单人旁写成两竖排列,整体方整。
图片
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这首古诗以《鲜于璜碑》的方正朴厚的风格为主,参合一些简帛书的书写感。通过蘸墨一次写多字体现墨色变化,并形成墨色对比。浓淡干湿枯的墨色变化,原作的墨色层次感更好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“瓜洲重山”的“瓜”撇捺左右开张,取横势,墨色因一笔写了几字了,故呈现半润半枯的状态。“洲”的墨最少,枯笔和飞白较多。且是左右结构,左边三点水处理成上下排列的三个点,右边的“州”左右排列,三个类似不同大小的“坐在椅子上的人”,一个“洲”字便有瘦高和宽扁两种姿态,怎能不生动?“重”处理成瘦高的整体排列多横,但是细节处课多做不同方向的变化,由于墨少再加上运笔的轻重快慢,形成枯笔和飞白,更显苍茫浑厚。“间钟又绿”的“间”墨最少,多枯笔和飞白,行笔宜慢,门字框左大右小,左曲右直,“间”的“日”处理成向左倾斜,在大的门字框架下,“日”做一些微小的律动,使得“闲”字充满生命力。饱蘸墨汁来写“钟”,与枯笔“间”形成强烈的墨色对比,创作是应注意繁体字的正确使用,例如:“钟”的繁体有两种写法:“鐘”和“鍾”,前者用于“鐘錶”、“時鐘”、“敲鐘”,后者用于“鍾情”、“鍾愛”、“鍾靈毓秀”。故本次创作的古诗“钟山”的“钟”应为“鐘”。“又”笔画少,可发挥曲线的灵动,撇捺伸展的同时注意方整浑厚,与其余三字形成“三密一舒”的小章法。“绿”的墨色减少,半枯半润,与“间”的墨色形成呼应,“绿”的绞丝旁采用篆书写法,写的更加茂密一些,“绿”是左右结构,采用左大右小,与“钟”的左小右大形成对比。“春风时照”的“春”采用篆书写法,处理成上下结构,墨色为半润半枯,与“风”的枯笔和飞白形成渐变。“风”多以枯笔和飞白为主,撇用飞白,展示飞动之势,撇低燕尾高,整体成向左倾斜的险绝之态。“时”用浓墨写就,再配以粗厚的线条,使得字内空间更加紧密,体现“密处不使透风”的书法原理。“照”上下结构,下方四个点紧密且圆厚,多点呈方向不同,趣味性更足,“照”的上部由三个部件组成,各有不同的倾斜姿态,若即若离的感觉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点赞、转发、关注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!
关注游庐,一起探索生活中的艺术美!
与诸君共勉!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
配资网app官方最新版本介绍,理财配资平台,生利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